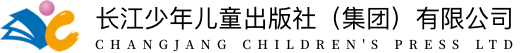《天涯芳草》是一本以博物視角講解植物知識(shí)的圖書(shū)。2024年,《天涯芳草》(第二版)面世。春暖花開(kāi)時(shí),我又翻開(kāi)了這本書(shū)。
大約是在2015年,我就買過(guò)這本書(shū)的第一版。那時(shí),我剛開(kāi)始觀察植物不久,書(shū)中講述的北方植物,如構(gòu)樹(shù)、山桃、沙參、毛櫻桃、白頭翁、迎紅杜鵑、螞蚱腿子等,令生活在北方的我倍感親切。對(duì)于書(shū)中的南方植物,我卻知之甚少,因此在閱讀時(shí)只是簡(jiǎn)單地瀏覽圖片,并未深入探究。當(dāng)時(shí)這本書(shū)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,是書(shū)中對(duì)于“咫尺天涯”和“天涯何處無(wú)芳草”關(guān)系的解讀——芳草在天涯,更在咫尺,關(guān)注日常生活中的大自然,也可以擁有無(wú)窮的樂(lè)趣和巨大的收獲。正是這本書(shū),使我堅(jiān)定了觀察身邊植物的決心。
時(shí)隔多年后閱讀《天涯芳草》(第二版),我的感受與之前大不相同。經(jīng)過(guò)這幾年的學(xué)習(xí),我已經(jīng)能夠辨認(rèn)出書(shū)中提及的大部分植物。現(xiàn)在最吸引我的,是書(shū)中關(guān)于地理、地質(zhì)和歷史等知識(shí),以及那些蘊(yùn)含其中的深刻哲學(xué)思想。
書(shū)中不時(shí)出現(xiàn)“兩側(cè)高崖以及半坡中偶見(jiàn)花崗巖(具體講是正長(zhǎng)石)”“抬頭向遠(yuǎn)處望去,流水……在巨大的磨圓度頗好的花崗石中間左突右奔……”這樣的語(yǔ)句,使畫(huà)面感更為具象化。除了植物和地質(zhì)知識(shí),書(shū)中還時(shí)不時(shí)穿插描繪了秀麗的風(fēng)景、奇妙的昆蟲(chóng)、特別的建筑,以及有趣的人文歷史故事。
在這本書(shū)中,知識(shí)與浪漫穿插交織。講到秋景時(shí),書(shū)中寫(xiě)道:“花楸樹(shù)可高達(dá)8米,火紅的葉子與藍(lán)天、白云相互映襯,坐在樹(shù)下或者躺在巨大的花崗石上,靜觀白云緩緩穿過(guò)花楸的羽狀復(fù)葉,什么也不用想,時(shí)光在悄悄地流逝,這種體驗(yàn)自然而神圣”。前兩句是客觀的知識(shí),到了第三句,文風(fēng)陡然轉(zhuǎn)為溫馨浪漫的詩(shī)意。
提出好的問(wèn)題是所有探究的基礎(chǔ)和前提,但遺憾的是,許多成年人已經(jīng)失去了提問(wèn)的能力。而本書(shū)作者劉華杰老師顯然是個(gè)“好奇寶寶”,有著超一流的提問(wèn)能力。發(fā)現(xiàn)校園內(nèi)一株被構(gòu)樹(shù)寄生的刺槐時(shí),他提出了這樣的問(wèn)題:在植物志或網(wǎng)絡(luò)資料中,是否有關(guān)于這種現(xiàn)象的記載?
為了解答這個(gè)問(wèn)題,他首先查閱了《北京植物志》與《中國(guó)植物志》,但沒(méi)有找到關(guān)于構(gòu)樹(shù)寄生現(xiàn)象的記載。然而,網(wǎng)絡(luò)上曾有報(bào)道指出,在南京植物園發(fā)現(xiàn)過(guò)構(gòu)樹(shù)寄生柏樹(shù)的案例。劉華杰老師推測(cè),這種構(gòu)樹(shù)寄生的現(xiàn)象可能是鳥(niǎo)類活動(dòng)的結(jié)果,并進(jìn)一步提出了幾個(gè)問(wèn)題:是哪種鳥(niǎo)“栽種”了這棵樹(shù)?這類事件發(fā)生的概率有多高?這棵構(gòu)樹(shù)的性別是什么?寄生者可以存活多久?最終是否會(huì)危害到寄主刺槐?校園管理部門是否會(huì)在某天決定將其移除??jī)烧叩哪举|(zhì)部是否會(huì)發(fā)生融合?跟隨這些問(wèn)題,讀者也會(huì)深入思考這一自然現(xiàn)象的復(fù)雜性和獨(dú)特性。
本書(shū)輔以大量照片,并配以簡(jiǎn)潔的文字。如果不讀正文,只“看圖說(shuō)話”,也別有一番“輕閱讀”的樂(lè)趣。
讀書(shū)的時(shí)候,我仿佛追隨劉華杰老師的腳步,踏進(jìn)生機(jī)盎然的荒野,聞花香、看葉落、撫溪水、沐山風(fēng),多識(shí)草木之名,天涯宛如咫尺。
(作者系《博物》雜志編輯李聰穎)

▲ 本文刊發(fā)于4月11日《科普時(shí)報(bào)》13版